日本战败已70载,对于战争的记忆仍然割裂着东亚
7月的夜晚,东京没有比靖国神社更宜人的地方了。走过两旁种满银杏树的大道,一路蝉声低鸣,不绝于耳,来到树木掩映、由深色的柏树梁木搭建而成的雄伟神门。拜殿前,绣有菊花纹饰的白幔撩人地随风摇曳。道路两旁灯笼高挂,身着浴衣的人群熙来攘往,沉浸在节日氛围中。人们抬着供有一方神灵的神轿,欢快地喊着号子。
靖国神社的御灵祭在8月15日到达高潮,这是日本二战战败纪念日。随着这一天的临近,通往神社的道路边摆满了摊档,喧闹狂欢如伦敦昔年的巴塞罗缪节大集市(Bartholomew Fair)。但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快乐,也有一些阴郁的人们,包括日本为数不多的幸存老兵及其家属,在这里悼念亡友。黑帮分子穿着贴身西装,趾高气昂;军事狂热分子佩着军刀或穿着神风队的飞行服,昂首阔步。有人在示威抗议,许多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而警察将他们维持在原地。
这里还有亡魂。没有他们,靖国神社就毫无意义。神社供奉的是为保卫天皇而战死者的灵魂,他们被尊为kami,这个词大致可译为“神灵”,虽然并不完全达意。神社建于1869年,即开启日本现代化的明治维新的第二年,庄严的仪式和大众娱乐从一开始起就相合相契,这让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人们惊讶不已。最初的大祭仪式伴随着烟火、炮声和相扑。
最初,这里供奉的神是明治维新时代内战中为天皇一方而战的阵亡者。随着日本占领台湾(1895)、朝鲜(1910)、满洲(1931)、中国东部沿海(1937)和东南亚(1941),所供奉的神灵数量和祭典的规模也越来越大。现在共有2,466,532名帝国保卫者被列入《灵玺簿》。他们全体被视为天皇的神盾。
根据神社的信条,所有亡灵都是平等的。但对全世界而言并非如此。一个民族要纪念其战争死难者,没人会反对,即便他们是出于恶因而战。但在1978年,靖国神社的宫司们悄悄地开始供奉14位政治军事领袖,包括战时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大将,他因计划并发动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的军事侵略战争被东京国际军事法庭判定有罪。这14人有的被日本的新领主美国处决,有的死在狱中。对许多人而言,包括很多日本人在内,将神圣荣誉授予这些人实在出格。数百万人为之献身的裕仁天皇不再参拜靖国神社;现任天皇明仁延续了这一做法。但是保守的民族主义政客却越来越多地参拜神社,包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这招致全球许多国家的告诫,也激起了中国和韩国的愤怒。
Video
还有些亡灵引人瞩目,他们没那么臭名昭著,但更辛酸凄凉。其中之一是李思炫,他的故乡是今天的首尔,但在1910年到1945年间被称作京城,是朝鲜日治时期的首都。在李思炫成长的20世纪30年代,他故乡的大部分城墙和宫殿都已被夷为平地,剩下的断垣残瓦只是为了让日本观光团足以感受到一些异国风情(朝鲜妓院也在游览路线上)。总督府的巨大穹顶占据了城市正中。为庆祝1940年第一代日本天皇登基2600周年(这纯属虚构)纪念而建的皇国民誓塔内,存放了140万朝鲜学生写下的效忠日本天皇的誓言。
李思炫的女儿李熙子生于1943年,当时日本已日薄西山。美国人正不断攻占日据太平洋岛屿,节节进逼。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始于1937年,本以为可以速战速决,结果遭到苦行坚韧的基督徒蒋介石委员长和他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抵抗,发展成大规模的长期战争。为了满足战争需求,朝鲜及其北方日据的满洲被剥削殆尽,资源和人民被洗劫一空。几千名朝鲜妇女被诱拐为军妓;几万名男子被迫到矿场和工地做苦工,地点主要在日本。自1944年起许多人被强征入伍,李思炫成为其中一员。1945年6月,就在战争结束前几周,他在中国南部的广东阵亡。
他的女儿如今已72岁高龄。就像东亚所有古稀老人一样,她经历的时代可谓波诡云谲。一如中国,李熙子的祖国也深受内战创伤,一分为二;后来又和日本和台湾以及再往后的中国一样,经历了经济腾飞,面貌焕然一新。人口翻了三倍,GDP翻了50倍。韩国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民主国家。身处这沧桑巨变的历史尽头,回望战争似乎已很遥远——在欧美,情况确实大体如此。然而在东亚,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意义上,无论是小到个人的生活细节还是大到国家间的外交关系,70年前结束的那场战争依然塑造着人们的世界观,左右着该地区的政治,也让亡灵难以安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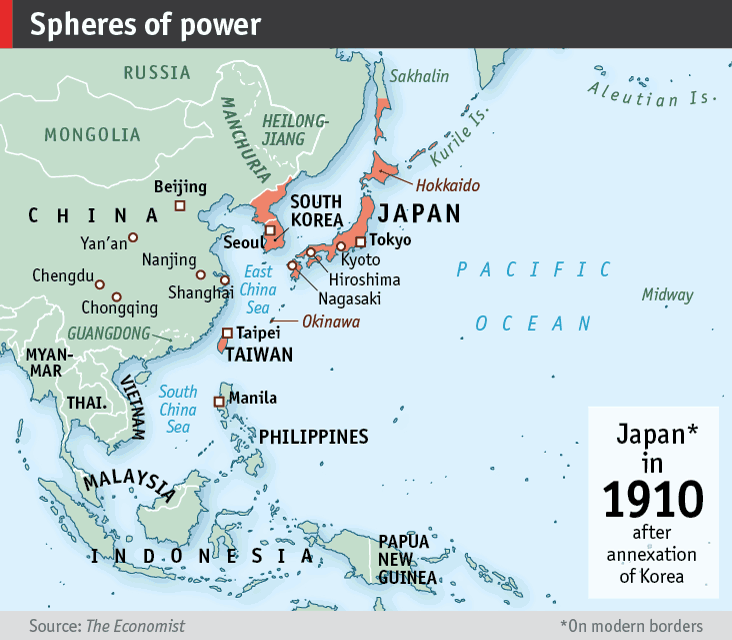
1959年,李思炫的亡灵悄无声息地被供奉进靖国神社。他为天皇而战死,因而成为了一名神圣的天皇护佑者。1996年,他的女儿发现此事,坚决要求将父亲的姓名和神位从靖国神社中移出。“我不是一名活动分子或学者,”她说道,“我只是我从未见过面的父亲的女儿。所以我认为我对他有一份责任:把他从靖国神社带回家。”她始终认为,父亲的栖身之地应该是首尔南部的天安,那里有史称“三一运动”的烈士纪念馆。1919年的那场运动中,数百万韩国民众走上街头,抗议日本殖民者的统治,成千上万的抗议者被血腥镇压,更多人则被关进了京城臭名昭著的西大门刑务所。
事实证明,在日本为亡灵搬家绝非易事。靖国神社的宫司们虽礼敬有加,但态度坚决。一旦亡魂被奉为神灵,无论如何都不能退出。李熙子求助于当地政府,官员们却告诉她,将她父亲的神位供奉于此,乃是对帝国士兵一视同仁的明证。然而李熙子强调,日本政府从未像对本国阵亡士兵那样,尝试找寻她父亲的遗体。
李熙子和其他急于把家人的神位从靖国神社移出的人一起,包括一些日本人在内,求助于法院,结果也不乐观。最新一批诉讼中,寻求从神社移出的名字中包括一位年长的原告,他被列为阵亡显然是夸大其词。但是即便还活着,看来也无法从灵玺簿中除名。显然,就算只是问上一问也是失礼。东京高院最近的一项判决称,原告们应当“包容他人的宗教自由”。
李熙子问道,为什么日本当局不能理解像她这种家庭所蒙受的屈辱?而这种屈辱本来很容易纠正。多位日本首相都曾为该国的侵略行为道歉,日本政府也承认自己在妓院里奴役妇女实属有罪。而且日本人同样明白人民被掠是什么感觉: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一些日本人被绑架到朝鲜,为残暴政权充当翻译和间谍。十多年前,安倍正是因为在此事件上直面朝鲜才成就了其政治声誉。每一天安倍都系上一条蓝色丝带,提醒自己记住那些受害者。李熙子问,难道安倍看不到她的父亲也是被绑架的吗?
但是,从来没有名字被从靖国神社中移出。
明治维新开启了世所罕见的现代化浪潮,甚至中国1978年以来的转型也无法与之媲美。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日本从狭隘的封建幕府变成了现代化强国,不仅是经济强国,也是军事强国。日本领导人从未忘记被美国炮舰强行打开国门的屈辱,那时的日本被赫尔曼·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称为“闭关锁国的土地”。因而日本喊出了“富国强兵”的口号。
1945年之后的70年里,日本没有因怒发过一枪一弹。在那之前的70年里,战争是日本发展的核心。其扩张始于1874年,当时它首次对台湾(外界称为“福尔摩沙”)进行了惩罚性的远征。1879年,它吞并了爱好和平的琉球王国,即如今的冲绳。1894至1895年,日本对清朝发动了主要发生在朝鲜半岛的甲午战争,战争以中国耻辱失败告终,中国几百年来在东亚的主导地位被日本篡夺。1905年,在朝鲜和日本之间的对马海峡,日本几乎让整个俄罗斯舰队葬身海底。这是100年前纳尔逊(Nelson)在特拉法尔加战役大胜以来最大的海战胜利,为日本随后未遇挑战就吞并朝鲜铺平了道路。
相比日本军国主义后来受到的谴责,日本的军事现代化在早期的几十年里受人钦佩,这很值得回味。和西方帝国主义列强一样,日本也为其帝国在海外的冒险披上了正义、合法和强力的外衣。这给西方列强留下了深刻印象,因而它们几乎无法拒绝在主桌上给自己的学生以一席之地,尽管这位俱乐部新成员很快就发现种族歧视的存在。
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们也赞赏新日本,包括未来共和制中国的奠基人孙中山。激进分子和知识分子齐聚东京,向这个亚洲强国学习,因为它可以在国内孕育自豪与繁荣,同时在海外与西方抗衡。这种赞赏甚至延伸到了靖国神社,正如它所体现的忠诚、自我牺牲和爱国主义的美德。19世纪90年代早期,中国知识分子和改革家王韬赞许地写到,“很容易理解日本政府供奉战争亡灵背后的意图:民众将热情澎湃,其忠诚将永不枯竭。”在那之后不久,中华帝国就败在了日本人手下。
正如它试图仿效的欧洲列强的帝国主义,日本的殖民主义植根于暴力,往往还有种族主义。然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变得异常混乱,原因与其说是追求更为强大国家的战略目标,倒不如说是对冒险主义缺乏控制。明治维新后掌握实权、对军队有约束力的最后一批政治寡头退出了舞台。1931年,作为既成事实,一小群军官向日本政府报告他们已经占领满洲。国际联盟谴责这一举动之后,日本退出了国联,并与纳粹德国以对抗共产主义为名建立了同盟。1937年,中国和日本军队在北京城外的卢沟桥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所说的纵贯中国东部沿海的“歼灭战”。
麻省理工学院研究日本的历史学家约翰·道尔(John Dower)强调,现代社会不以侵略之名动员参战,日本也不例外。在日本国内,其侵略被描绘成对合法权益的保护,或者是对抗共产主义的无私斗争。西方殖民势力的谴责被斥为非常虚伪:亚洲国家饱尝西方殖民主义之苦,日本是它们的拯救者和天生的领导者。泛亚主义是日本对外扩张的哲学基础,有时候还是精神基础。道尔指出,对日本而言,它大肆征服、力争创造“大东亚共荣圈”的那几年是一个“美丽的现代战争”时期。
许多保守的日本民族主义者仍然看到那一时期的美丽。安倍相信日本当时寻求富国强兵从根本上是正确的,今天依然如此,同时,重新实施这一政策是日本恢复成为一个其他人所称的“正常”国家的关键。而安倍所称的“战后时期”则是日本历史上一段可耻的例外,要依赖美国的保护,还有限制日本海外空间的宪法。
采取这样的立场并非是否认日本所犯的恶行。首尔延世大学(Yonsei University)的东亚历史学家鲁乐汉(John Delury)认为,相反,这一立场相信日本帝国在战争中的表现与其他国家没什么不同。其他国家也犯下了严重错误。历经轰炸之后硝烟弥漫的东京即是见证,十万人亡命于此;广岛和长崎被原子弹轰炸也是见证。基于这一观点,历史没有让日本人承担特别需要表达悔恨或歉意的义务:“事实上,认为没有必要表达特殊的悔恨就是日本迟来的回归常态的一种表现”。
回到靖国神社,它沐浴在美丽的谎言之中。参观其博物馆“游就馆”的人们会发现,当初使日本败亡的军国主义仍被美化。令人畏惧的自杀武器被尊奉,包括回天(“回到天堂”)鱼雷。这是一个15米长、内置一个微型座位和一个小型潜望镜的黑色哑光抛射体,实际上就是一件水下自杀背心。日军在南京(1937年)和马尼拉(1945年)的暴行被轻描淡写或者矢口否认。在那里,日本士兵肆行杀戮与强奸,屠杀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平民和战俘。一直以来,战争的目的被描绘得高尚而纯洁:日本作为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共产主义或者中国军阀混战的堡垒巍然屹立。
2013年底,安倍晋三履行竞选时的诺言,参拜了靖国神社,掀起了一股外交风波。中国在全球各地的外交官纷纷发表署名评论文章,旨在激起反日情绪。在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上,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称靖国神社是“一种魂器,代表了(日本)灵魂的最黑暗部分”。他料想读者们会知道,在哈利·波特的世界里,魂器存放着从身体中分离出去的灵魂的一部分,以期得到永生,而且魂器只能通过谋杀才能制造。他希望读者们能推断出,安倍晋三就是新的伏地魔(Lord Voldemort)。
这是修辞上的神来之笔,也不止于略带虚伪。中国共产党也有自己的魂器,直至不久前仍把一切不朽期盼寄托其上,那就是毛泽东的遗体。他的暴力统治令数百万国人死于肃清运动及饥荒。但1976年他离世后,在象征中国权力中心的天安门广场上,建起了一座巨大而丑陋的纪念堂来保存他的遗体。那肉身经过防腐处理,但仍不免于一点点慢慢腐烂。
毛泽东是中国统治者掌权合法性的必要来源,但已不再是充分条件。人们已有足够认识了解他当权时的暴力及暴政,就连共产党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功过要“三七开”。随着中国经济及外交影响力日增,声誉对其统治者来说有着新的重要意义,这是毛泽东从来不曾真正关心的,况且其遗留的影响对中国的声誉也毫无帮助。于是,一股复兴民族主义思潮与经济增长和军事实力共同构成了“中国梦”的一部分,而这一民族主义在诠释上,首先是以战时日本侵略为对立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显然把对抗战的回忆视为塑造中国人认同的工具。
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对中国当年在二战中所起的作用的记忆应该在外国也很重要。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建基于其击败日本的战绩。中国在该区域的领导地位同样是因为在打败日本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毕竟正是这一角色让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之一,当时只有战胜国才能获得这一席位。在刘晓明大使那篇“魂器”评论文章中,他提及当年中国士兵与盟军部队“并肩”作战。上个月,他邀请笔者参加纪念8月15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庆典。
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当然值得重新评价,正如牛津大学的拉纳·米特(Rana Mitter)在其最近一部关于中日战争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Forgotten Ally)中所提到的。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迫使美国参战,期间中国一直孤军抗日。米特认为,假如中国在1938年投降——这在当时看来极有可能——东亚地区这几十年也许已成日本的大帝国。相反,中国坚持抗战,付出了巨大代价。在1937年至1945年的战争中,约有1500万中国士兵及平民丧生,一亿人沦为难民;参战的其他国家中,只有苏联的损失可同日而语。诚然,中国最后没能打败日本,但其顽强抵抗牵制了数十万日军。
这是习近平强调需要被认识的一段历史,但这里面有中共不愿面对的真相。几十年来,共产党官方叙事甚少提及国民党和蒋介石,若有触及,也是以反共势力的面目出现:太懦弱、腐败、不爱国而不能抗击日本。中国的“解放”并非在1945年,而是在1949年——那是日本败退后共产党在内战中打败国民党的结果。就这样,共产主义对民族主义的胜利被塑造为中国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终点。
但实际上,那些反对帝国主义、怀有强烈民族主义的国民党才是抗击日军并将其拖入更深泥沼的主要力量。正是他们与亿万中国平民在八年抗战中患难与共,坚毅反击。相比之下,共产党的抗战根据地规模较小,而且相对安全。假如国民党当初没投入那么多军力在抗日上,蒋介石很有可能会在随后的内战中获胜。
中国的这段历史在战后几十年一直被极力打压,如今正被谨慎而有选择性地重现为新时代民族主义的一部分,藉以表达其在地区与全球的抱负。其中一个作用是把台湾(蒋介石及国民党在1949年撤离至此)和中国大陆讲述的故事连结起来,强调中国人对抗日本侵略的共同奋斗,而非内战造成的分裂。然而,除了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这也是因为一股新期盼渐渐从地方冒升——中国以前被边缘化的一些地区要讲述自己的战争故事。
在中国西南,重庆某全新城郊小区的一套大户型公寓里,身穿花睡衣、身材矮小的王素珍被家中三代老少围绕着,身陷在宽大的人造革沙发里。对面是覆盖整面墙壁的大电视,正在播放着一档展现父母爱宠儿女的真人秀节目:一位父亲带穿着蓬蓬裙的小女孩去上芭蕾舞课;一个戴着墨镜的小皇帝驾驶着小型宝马模型车。室外的重庆如同狄更斯笔下的时代,满目雾霾,而那炎夏热火几近地狱煎熬,长江浊流滚滚,在峭壁之间蜿蜒。
1938年,蒋介石与其政府撤退到重庆。前一年,当时中华民国的首都南京在大屠杀中沦陷,日本侵略者的这场恶名昭彰的胜利使其控制了中国几乎所有沿海城市,包括上海。几百万中国人跟随蒋介石逃亡到重庆,这里成为当时中国的陪都,直至战争结束。
那是艰难困苦的七年。虽然位处偏远和山区地形在一定程度上给这个城市带来了保护,但战争仍然就在眼前。许多平民在空袭中丧生,而在1941年6月5日的一次事故中,一个防空洞里就约有1500名平民死于窒息。政府开出每具尸体一斤米的条件,让船夫们把这些尸体运出城外。
王家比大部分人过得好一点。他们住在重庆城外的石龙镇,躲过了空袭。就在日本投降六天后,王素珍出生。不久后,王家搬到重庆城里,在城里的批发市场卖丝绸刺绣谋生。但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改变了这座城市。重庆作为抗战中心的战时光辉历史受到打压。抗战胜利纪功碑被更名为人民解放纪念碑。带有“坏”阶级背景的人(即随蒋介石来到此地的恶“地主”和国民党人)被贴上耻辱标签,王家被迫离开重庆搬到农村。
王素珍的母亲在农村公社里辛勤劳作,努力养育八个儿女,然而,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轮番袭来。王素珍记得,某个冬天,生产队弄来了一头牛,但因为没有草吃而快要饿死。然后,人们自己也开始吃草为生,引致腹胀,有时吃了草也照样饥肠辘辘。后来,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把恶“地主”拽出去殴打。“我们什么也没问,” 王素珍说道,“我们不敢出声,不然,我们也会被打。”
1987年,王素珍和家人离开了公社,自己种植和销售农作物,日子过得不错。政府给她当老师的女儿分配了一套房子,他们全家搬了进去。1989年,他们买了第一部电视机,还有一台冰箱。2005年,他们买了第一辆汽车。家中谁也没想到一切会变得这么快。几年前,王素珍还找到了精神慰藉。事缘一位年长亲人去世,之后她觉得家里冤魂不散。他们找到一位道家天师来安魂,但不奏效。“然后一些基督教朋友说他们那种祷告能带来安宁,果然如此。”那鬼魂不再困扰他们家,王素珍现在每周都去教堂。
王素珍的信仰之路有点异乎寻常,但她家的致富轨迹在这城市里则相当典型。随着西南日渐富裕,人们开始更公开地谈论本地的战时经历。以往,每逢8月15日,重庆的报章总是刊出同样的国家叙事,跟你在北京读到的没有两样。如今,他们会向当地的战时英雄致敬。1941年防空洞惨案所在地被定为纪念遗址。在黄山山顶,蒋介石曾藏身的旧居内,会有一位年轻演员身穿委员长的儒雅长袍,贴上小胡子,在那里迎接游人。
假如重庆正重拾过往历史,而且全中国渐渐认识到,在对抗帝国主义势力的过程中,不单共产主义,民族主义也起了重要作用,那么,这对中日关系有何意味?有迹象显示,这或许会带来改善;更复杂细致地去看待中国历史才能令人更细致入微地看待其敌国。
Video
乍看之下,王素珍还是坚持传统看法:她激烈地说,日本人很残忍,她不喜欢他们。她遇见过日本人吗?没有,她承认,但又对着电视机点头,说她经常看得见他们。当被提醒那些抗战影片里的日本人都是中国演员扮演的,她笑了起来。“那只是政治宣传,我知道。” 说完,她又和家人一起沉浸在穿粉色蓬蓬裙女孩的故事中。
习近平以旧日的敌对情绪来支撑现代的民族主义认同,这令人担忧。但一个比中国过往任何时期都更富裕的社会,还有许多其他方面影响到其价值理念的塑造。像在强调这一点似的,王素珍既是对自己又是对笔者低语道:“谁会想念过去?”
与安倍晋三心灵相通的并非只有靖国神社的鬼魂。2012年大选获胜后,他径直到外祖父岸信介的墓前许下诺言。岸信介也曾任首相,于1957至1960年间在位。虽然他是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者,但面对日本向美国投降而后被阉割沦为小跟班的战后角色,他不得不接受要以重振经济为重,回归大国地位为次。当然,这只是个权宜之计,岸信介很清楚这一点。
1965年,岸信介认为日本有必要重整军备,作为“全面清除日本战败及美国占领结果的手段。有必要让日本最终走出战后年代,让人民重拾作为日本人的自信和自豪感”。这些言辞放在安倍的竞选宣言里也毫不违和。而安倍在外祖父墓前立下的誓言是他将为日本“重拾真正的独立”。
这不意味着安倍反美。像他外祖父一样,安倍需要美国来确保其国家安全。面对中国的崛起,他加强了两国的军事同盟,4月时同意签署了新修订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但他对美国在“日本衰败史”中所扮演的角色深有介怀,这里不是指战时的实体破坏,而是美国在战后强加的秩序。他讨厌东京的战犯法庭:一边绞死了征服亚洲的日本领导人,另一边西方列强又重新确立了它们在亚洲殖民地的统治,这是何等虚伪。他认为加诸本国的宪法限制了日本的正当抱负。在教育界,左翼人士合谋灌输战争罪恶感及对爱国主义的反感。
这一战后秩序对随后70年的和平、繁荣、民主发展所起的作用在这样的分析里被忽略,要知道安倍的自民党正是这段时期的一大受益者。但美国也没有资格以双重标准指责日本的民族主义者。毕竟,尽管一切战争罪行都是以裕仁天皇为核心的政治体系以其名义犯下的,但当时麦克阿瑟将军决定不起诉天皇,他的理由无法被证明正确但令人难以置信——他认为一个被击溃的民族若能保留其皇帝会更顺从听话。正因为这一决定,日本更难以检讨自己的行动,也难以为其受害者或为国家自身全面记录这些行为。但冷战抹去了最后一线清算机会,因为美国需要资深的日本保守派作为盟友。东京的战争法庭对第一批日本战犯宣判后,几乎同一时间,以甲级战犯罪名被起诉的其他人便从东京的巢鸭监狱获释,继而被委以高位。
其中显眼的一员是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满洲国傀儡政府的背后主脑。通过把私人资本运用到由政府高度主导的经济中,他把满洲国变成了日本战争机器的发动机。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的马克·德里斯科尔(Mark Driscoll)曾描写过这一体系虐使中国劳工的一套“死亡政治”观。这个超现代的试验性政权残酷运用人力的历史如今几乎已被遗忘,但这一结合私人资本与政府高度主导的方法不但直接启发了日本在战后的发展,而且,之后韩国和中国也相继从中得到灵感。而这一切的背后主脑是谁?正是岸信介本人。
安倍不加批判地认为其国家的本质与明治维新的建制及之后催生的一切密不可分,这是执迷不悟。但如果否认日本在战前和战后的连续性,认为一切是割裂的,那同样不对。四方八面,鬼魂被紧锁禁闭。相反,应该让它们说说,也听听——倾听、诉说战争的复杂真相,讨论责任何在,回忆受害经历。
徐明回想起第一次独自出门的情景,那时没有母亲在旁牵着她的手。她问一群小孩能否让她加入一起玩。“‘不行’,其中一个孩子说。‘为什么?’我问。‘因为你是个小日本鬼子’。然后最高的那个孩子插嘴说,‘行,可以一起玩。但你要做狗。你得在我们裤裆下爬过去,然后汪汪叫’。我照他们说的做了。然后他们开始打我。”
1944年,徐明在中国东北的黑龙江出生,那里是满洲的一部分,3年前岸信介已从那里被召回东京担任工业大臣。徐明是家中独生女,父母爱护备至。但她在外面却备受欺凌。七岁时,班级组织观看一部战争电影,讲述的是共产党军队打击穷凶极恶的日本人的光辉战绩。她身边的孩子开始高喊“打倒日本人”。然后他们朝她吐口水。看完电影,老师点名,但徐明不见了。老师发现她蜷缩在椅子下面,眼睛哭得通红。老师批评了班上学生。她说,徐明只是个孩子,电影只是电影。那天,徐明立志要成为一名教师。
一年后,一名公安来到她家。徐明被打发到屋外,但她伸长脖子偷听里面的对话。那位官员大喊:“你最好承认:这孩子是日本人,是你收养回来的。”她母亲泪流满面。徐明跑进屋里安慰她。两母女哭得一塌糊涂,哭得那名公安也问不下去了。
就是那个时候,徐明问:“我真的是日本人?”
“对,”她母亲回答道,“你是。”
据约翰·道尔称,战争结束时有超过600万日本人滞留海外。很奇怪,他们的故事少有提及,即便在日本也是如此。滞留的日本人中约有一半是士兵,许多人受伤、体弱或患病。其他有管理人员、银行职员、铁路员工、农民、工业家、妓女、间谍、摄影师、理发师、孩子。对于这些人以及他们在日本的亲朋好友来说,8月15日远非彻底结束之日。被征召入伍和流放外国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也陷于类似的境况。日本战败一年后,还有200万日本人没有回国。许多人再也没能回去。日本在1946年推出全国性电台节目《失踪人士》,直至1962年才停播。
盟军利用了投降的士兵。其中七万人被美军用作其太平洋基地的劳工。莫大的讽刺是,英国人利用了超过十万日本人在东南亚部分刚被“解放”的地区重申殖民统治。在中国,数以万计的日本人加入内战双方作战。
最糟糕的命运是落入俄国的“保护”。在最后一周参战的苏联接受了满洲及朝鲜半岛北部日军的投降。可能有160万日本士兵落入苏联手中。约62.5万人在1947年底被遣返日本,许多人之前曾被送往西伯利亚的劳改营,并受到密集的思想改造。其他一些人成功南下,去到朝鲜半岛上由美国控制的地区。1949年初,苏联声称只有9.5万名日本人有待遣返,但据日本和美国的计算,还有超过30万人下落不明。
1945年8月,仍有100万日本平民留在满洲。据猜测,在日本投降后的混乱和苏联的暴力之下,其中约有17.9万人在企图回国时丧生,或是死于1945至1946年间的严冬。孩子们回到日本时已沦为孤儿,脖子上挂着装有家人骨灰的盒子。在满洲,日本父母恳求中国的农民家庭收养他们最年幼的孩子。
徐明的生母就是这样做的。她生父在日本军队服役,已被强拉至西伯利亚。小徐明是他们最小的女儿,她母亲觉得这孩子熬不过回日本的旅程,便恳求一对夫妇收养她。后来这对夫妇生了好几个孩子,便把小徐明卖给了徐家。
Video
多年过去,徐明终于通过考试成为一位教师。她成绩优异,本来事业前景一片美好。但之后几年,她只能在黑龙江深山老林的晦暗营地里给伐木工子女教书。“你没法改变的,”她的教授曾说,“你是个日本人。”在木材营地里,人们只能把玉米苞叶和树皮磨碎来做面包。但在如此偏远的地区生活却让徐明躲过了文革时期最严重的疯狂。在她的家乡,一位温柔勤恳的日本牙医被拉到十字路口,脖子上挂着谴责她是日本间谍的牌子。每次被问到是不是间谍,她都否认,然后就被打。三天后她死了。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为这昔日敌国启动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双边援助项目。日本人开始来到黑龙江寻找家人。一名来访记者答应徐明,会替她在日本媒体上登广告寻亲。北海道的一位老兵回应了其中一则广告,肯定她是自己的女儿。在1981年,徐明获得了签证。能到日本去,她非常兴奋。她与那位老兵相见的场面十分感人。但之后的DNA测试表明他们并无亲缘关系。那位老兵再不愿与她有任何瓜葛。
日本官员威胁要驱逐徐明出境:中国法庭承认其日本血统的文件毫无作用。为留在日本,她奔走于各个法庭,期间她在当地一家非政府组织做志愿者,帮忙处理“满洲孤儿”事务。一天早上,在附近一家咖啡店里,两位正要前往这家非政府组织的日本女士问徐明能否同桌。当然可以,徐明用仍带有口音的日语回答道。两位女士问她是否中国人,如果是,来自哪里?黑龙江,徐明回答。我们的母亲当年正是把妹妹留了在那里,两位女士说。巧合之处越聊越多:说的是同一个镇,收养徐明的第一家人姓李,李家就在铁路旁边。自1945年以来,三姐妹第一次相见。现在徐明才知道自己的本名叫池田澄江,重逢固然欣喜,但得知她们的母亲几个月前刚刚去世,又难免哀伤。但如今,至少母亲的灵魂可以安息了。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经创伤的众人已接近生命终点。但包含他们印迹的亚洲历史继续塑造着其子子孙孙的世界。在某些地方,历史被扭曲,在另一些地方,历史被否认。某些受害者和某些胜利者得到人们的纪念。其余的被遗忘。
上世纪60年代,靖国神社里心态较今日开放的一位大宫司在神社空地的一个角落立起一个小小的神龛,供奉敌方亡魂。现在,这里围上了金属护栏,禁止游人接近。每年7月的祭日,一位年轻宫司会在神龛外面随便放一碗水果作为祭品,然后步履歪斜地走开。至于那场侵略战中的日本受害者——那些被将帅抛弃而在新几内亚丛林里死于饥饿和疾病的年轻士兵,以及因战事波及日本本岛而丧生的数十万平民:他们无处可见。靖国神社只纪念光荣的死亡。
“谁会想念过去,”重庆的王素珍坐在沙发上问道。的确,谁会呢?但过去不该就此遗忘。




